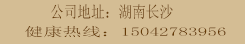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小血管炎 > 血管炎形成 > 嗜中性粒细胞在抗病毒免疫中的作用ld
当前位置: 小血管炎 > 血管炎形成 > 嗜中性粒细胞在抗病毒免疫中的作用ld

![]() 当前位置: 小血管炎 > 血管炎形成 > 嗜中性粒细胞在抗病毒免疫中的作用ld
当前位置: 小血管炎 > 血管炎形成 > 嗜中性粒细胞在抗病毒免疫中的作用ld
在岁末年初之际,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导致的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年1月7日,该病毒被鉴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nCoV,即年的新型冠状病毒;2月13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又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2月8日,在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ewcoronaviruspneumonia,NCP);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冠肺炎更准确命名为COVID-19。截止2月16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病例例,累计死亡病例例[1]。这场疫情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健康和稳定都造成重大影响。
病毒是自然界存在的非细胞形态的生物实体,自身无法独立存活,其生存与复制必须依赖具有细胞形态的生物。按照宿主特异性可分为动物病毒、植物病毒、细菌病毒(噬菌体)等;根据其遗传物质也可以分为DNA病毒、RNA病毒、朊病毒。而导致此次疫情的冠状病毒在系统分类上属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冠状病毒属(Coronavirus),因为被命名为SARS-CoV-2。
尽管冠状病毒上世纪60年代即被发现与命名,但真正使人们意识到其危害性的事件是于~年爆发的“非典”(HumanSARSCoV,共导致近人感染,人死亡)和于~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导致人感染,人死亡)[2]。冠状病毒进一步可分为α、β、γ、δ四种亚类,其中α/β型冠状病毒倾向于感染哺乳类动物,而γ/δ型冠状病毒倾向于感染鸟类;目前已知的可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均为α/β型冠状病毒,而SARS-CoV-2是第7种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其余6种分别为:HCoV-E,HCoV-OC43,HCoV-NL63,HCoV-HKU1,SARS-CoV和MERS-CoV),而对人类具有较大危害性的冠状病毒均为β型冠状病毒[3]。通过测序比对,研究人员对SARS-CoV-2的起源进行了推断。数据显示SARS-CoV-2倾向于一种蝙蝠来源的冠状病毒,和“非典”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相似性分别为HumanSARSCoV-79%,MERS-CoV-50%,而和一些类SARS-蝙蝠来源的冠状病毒的相似可以达到96%(bat-SL-CoVZC45andbat-SL-CoVZXC21)[4]。这基本可以作为SARS-CoV-2来源于蝙蝠的证据,后进一步确定这一病毒最可能来源于中华菊头蝠(Rhinolophussinicus)。虽然SARS-CoV-2和SARS-CoV的遗传基础仍有差异,研究人员证实SARS-CoV-2与SARS相似,均以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enzyme,ACE2)作为靶点侵入细胞。ACE2在正常生理状态下的功能是将血管收缩血管紧张素II转化成血管收缩血管紧张素1~7实现血管舒张,促凋亡,抗增殖等的目的[5]。研究人员在发现ACE2是SARS-CoV入侵靶点后,以此为基础,也对ACE2相关的抗病毒感染进行了研究,这些成果同样对于抗击SARS-CoV-2的感染有借鉴意义。
图1不同冠状病毒之间的亲缘性比较
(AipingWuetal,CellHostMicrobe,)
在千万年的进化中,机体也发展出了抗击病毒入侵的机制。病毒感染机体触发机体的免疫反应,各类免疫细胞即被激活,发挥抗病毒效应。在抗病毒免疫的过程中,嗜中性粒细胞的作用尚无准确的定论。在健康人体中,嗜中性粒细胞以40%~75%的占比(neutrophils/mcL),是免疫细胞-白细胞的最大的细胞亚群,在先天性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嗜中性粒细胞可以通过吞噬,释放溶菌酶和形成嗜中性粒细胞细胞外陷阱(Neutrophilextracellulartraps,NETs)的方式杀灭感染的细菌、真菌[6]。但在抗病毒免疫中,嗜中性粒细胞似乎在拮抗病毒感染的同时,会造成组织损伤,从而增加感染的严重程度。甚至有研究人员发现在小鼠模型中,消除嗜中性粒细胞或局部引入过多的嗜中性粒细胞均不会造成小鼠病症的加重或减轻。本文将整理报道的嗜中性粒细胞的各类角色,分析嗜中性粒细胞在抗病毒免疫中的真正定位,借鉴嗜中性粒细胞与ACE2的相关研究,并展望嗜中性粒细胞和COVID-19治疗的相关线索。
1.嗜中性粒细胞可拮抗病毒感染
在流感病毒(influenzavirus)感染实验中,研究人员事先通过anti-Ly6G抗体清除了大量小鼠体内的嗜中性粒细胞,结果证明嗜中性粒细胞清除组具有更高的感染死亡率。而在病毒感染后清除嗜中性粒细胞,对于感染病毒滴度和存活情况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但增加了小鼠受病菌感染的风险和程度。这些间接表明嗜中性粒细胞对于流感病毒感染有拮抗作用[7]。
目前的研究发现嗜中性粒细胞不仅可以被细菌、真菌感染所激活,也可以对病毒感染发生响应。单纯疱疹病毒(herpessimplexvirus,HSV)和人巨细胞病毒(humancytomegalovirus,CMV)进入嗜中性粒细胞后,会激活嗜中性粒细胞产生大量的活性氧(reactiveoxygenspecies,ROS),从而激活整个免疫系统投入到抗病毒免疫的战斗中。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syncytialvirus,RSV)导致嗜中性粒细胞产生ROS反应的同时,还释放IL1β信号,刺激感受细胞凋亡。嗜中性粒细胞间接参与抗病毒免疫的表现之一还在于激活获得性免疫系统参加抗病毒免疫[8]。Thelper1(Th1)型细胞和CD8T细胞是获得性免疫系统中,发挥抗病毒免疫的重要细胞。在流感病毒感染中,由嗜中性粒细胞或NETs所释放的粒蛋白和颗粒作用于树突状细胞(DCs),通过TLR9通路激活DCs作为抗原呈递细胞的作用,促进Th0型细胞向特定类型的Th1型细胞分化[9]。Th1型细胞会介导以干扰素为主的抗病毒机制。干扰素可降解病毒的核酸成分,激活NK细胞,并辅助NK细胞以细胞表面的MHCI表达水平下降为标志识别并杀灭感染细胞[10]。同时,嗜中性粒细胞可以发挥类似抗原递呈细胞的作用,直接激活抗病毒CD8T细胞,分泌干扰素等抗病毒蛋白[11]。更重要的是,嗜中性粒细胞的激活意味着整体免疫系统的快速觉醒。激活的嗜中性粒细胞可分泌更多的细胞因子,如IL1α、IL1β、IL6、IL7、IL18和MIF等激活强化整体的免疫系统参加抗病毒免疫反应[12]。
图2嗜中性粒细胞强化免疫应答
(PaulHasleraetal.SwissMedicalWeekly.)
而嗜中性粒细胞对抗病毒免疫的直接作用,主要是通过NETs实现的。NETs是嗜中性粒细胞对抗病原感染,尤其是病毒感染的重要工具。部分嗜中性粒细胞在受到外界病原(包括病毒、细菌、真菌等)或化学物(PMA,离子霉素)或内部血小板破裂等因素刺激下,细胞核染色质构象改变,形成的特殊结构。经典的NETs形成过程(Netosis)为:嗜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utrophilelastase,NE)降解接头组蛋白H1和核心组蛋白,导致染色质缩聚;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增强了染色质的缩聚。与此同时,肽基精氨酸脱亚氨酶4(peptidylargininedeiminase4,PAD4)催化组蛋白H3瓜氨酸化(精氨酸残基→瓜氨酸残基)[13]。最终形成的NETs结构一般粘附于血管内壁,其伸出的染色体片段上含有嗜蓝颗粒、MPO、粒蛋白、组织蛋白酶G、α防御素等成分可以拮抗病毒感染。研究人员使用PAD4缺陷的小鼠(不能产生NETs结构)在进行FeLV、HIV-1和influenzaA感染实验时,其感染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显著高于野生型小鼠。这也从检测证明了NETs对于病毒有杀灭作用[14]。
图3NETs形成过程
(MarcinZawrotniaketal.ActabiochimicaPolonica,)
2.嗜中性粒细胞在抗病毒免疫中的负面作用
在嗜中性粒细胞对抗细菌和真菌感染的过程,吞噬和释放溶菌酶也同样是重要的方式,但是在对抗病毒感染的过程中,嗜中性粒细胞主要依赖于形成NETs的方式。大多数嗜中性粒细胞即使在经历凋亡或坏死过程后也不会形成NETs,但是由于免疫系统被激活,导致NETs的绝对数目增加。受病毒感染的病灶处会分泌IL8招募循环的嗜中性粒细胞到病灶处形成NETs。大量的NETs浸润所释放的ROS、MPO等成分,会导致免疫系统被过度激活,对局部的组织和器官造成损伤。而这种由NETs造成的粘膜屏障系统的损伤,也加剧了病毒和外界其他病原的感染[15]。
NETs也会导致除感染以外的并发症,包括自身免疫细胞疾病和心血管阻塞。尽管自身免疫疾病的形成十分复杂,但在小血管血管炎(smallvesselvasculitis,SVV)和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lupuserythematosus,SLE)的患者中观察到NETs的聚集。而向患者体内注射抗嗜中性粒细胞细胞浆的抗体(ANCA)可缓解病症。而有超过70%的NETs成分和SLE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有效自身抗原成分是一致,消除NETs也可以缓解SLE的症状[16,17]。这些疾病都和NETs导致的免疫系统过度激活有关。而粘附于血管内壁的NETs会结合“网住”血管中的红细胞和激活的血小板,逐渐形成血凝块,进而形成血栓,损害心血管健康[18]。
图4嗜中性粒细胞对血管损伤
(MarcinZawrotniaketal.ActabiochimicaPolonica,)
嗜中性粒细胞的大量浸润还以ROS途径发生对组织的损害。ROS本身是作为调节细胞生长,细胞与其他细胞粘附,分化,衰老和凋亡的信号分子[19]。在炎症情况下,浸润的嗜中性粒细胞NADPH氧化酶活性、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激增,呼吸作用增加,形成了聚集的具有强氧化能力的还原代谢产物[20]。ROS干扰着生物大分子的电位和构象稳定,包括对DNA和蛋白质的基团修饰和化学键的断裂。生物膜系系统的表面分布着调节细胞信号的不饱和脂肪酸链也会被ROS破坏,造成生物膜流动性差,信号紊乱,最终导致组织损伤。
此外,还有研究人员指出嗜中性粒细胞可能可以作为某些病毒的“交通工具”。作为人体中占比最大的免疫细胞亚群,在血液循环的各处均有较高的比重。研究人员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发现了由西尼罗河病毒(WestNileVirus,WNV)感染的嗜中性粒细胞。并且当WNV病毒感染血管内皮细胞时,会促进其分泌IL8和C-X-C趋化因子来招募嗜中性粒细胞迁移到这一区域[21]。因此,研究人员猜想WNV在招募到嗜中性粒细胞之后,感染嗜中性粒细胞,并以此为工具循环于血液系统。研究人员随后发现H5N1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psteinBarrVirus,EBV)也有相似特点[8]。但是SARS-CoV-2似乎不具备入侵并挟持嗜中性粒细胞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条件。研究人员检测了全身各组织的ACE2表达情况,发现ACE2主要表达于肺部和小肠的上皮细胞[22]。近来又有学者对肺部各类细胞进行单细胞测序,发现仅0.64%的肺部细胞表达ACE2,其中83%为II型肺泡上皮细胞,占II型肺泡上皮细胞的1.4%±0.4%,而表达ACE2的浸润免疫细胞有单核细胞,巨噬细胞,DCs[23]。嗜中性粒细胞不表达ACE2,即SARS-CoV-2不能以此靶点入侵嗜中性粒细胞。
图5ACE2在肺部细胞的表达情况
(YuZhao1etal,bioRxiv,)
3.嗜中性粒细胞可能是抗病毒免疫的“旁观者”
可能由于嗜中性粒细胞在抗病毒感染的过程中同时存在正面和负面的作用,这就导致在宏观上难以判断嗜中性粒细胞对于抗病毒免疫的意义。年1月份的一篇文献中,研究了嗜中性粒细胞对于RSV感染的意义。研究人员先是在感染前通过anti-Ly6G的抗体清除了掉嗜中性粒细胞,再进行RSV的感染实验。结果显示,anti-Ly6G处理组的的病毒浸润滴度和炎症细胞因子浸润情况与isotypecontrol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虽然anti-Ly6G组和未处理组,未感染组相比,部分指标有差异,但是没有表现出规律性。并且,各感染组小鼠体重没有显著性变化。研究人员又通过CXCL1提高肺部嗜中性粒细胞的浸润,结果和之前相似,即提升嗜中性粒细胞的浸润并没有改善RSV感染症状,各组小鼠体重变化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别[24]。
不过,这篇文章的实验设计仍存在某些欠缺之处。首先,实验中RSV感染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病症,没有导致小鼠在感染后一定时限内死亡,部分指标可能不显著。实验指标中也存在感染组和未感染组无显著差别的情况。其次,实验中不能以存活率来进行分析,而以体重变化作为整体健康指标又太笼统。此外,研究人员也没对NETs等嗜中性粒细胞抗病毒机制进行研究。这些也动摇着嗜中性粒细胞在RSV感染,乃至病毒感染中的“旁观者”理论。
讨论:
COVID-19是由SARS-CoV-2所引起的造成大量人员感染死亡的公共卫生事件。目前还没有嗜中性粒细胞在抗SARS-CoV-2的机制研究报道。之前的研究人员报道了嗜中性粒细胞拮抗同为冠状病毒的肺炎大鼠冠状病毒的机制。嗜中性粒细胞对于抗击肺炎大鼠冠状病毒的免疫反应是必要的。去除嗜中性粒细胞会加剧肺炎大鼠冠状病毒感染的严重程度。不过,文章也同时肯定了嗜中性粒细胞在抗病毒免疫中,对机体血管内皮、肺泡等组织会中造成组织损伤,增加感染其他病原的风险[25]。由此可见,嗜中性粒细胞在抗病毒免疫中更倾向于一种双刃剑的角色。
ACE2作为病毒感染的靶点,也是一个潜在的治疗方向。研究人员曾对细菌感染的肺炎模型中ACE2和浸润嗜中性粒细胞的联系进行过报道。他们发现ACE2的表达水平和嗜中性粒细胞的浸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26]。即清除ACE2会导致肺部浸润的嗜中性粒细胞数目激增;补充外源性的ACE2可以减少肺部浸润的嗜中性粒细胞。进一步,他们发现ACE2可降低肺部细胞的STAT3信号通路,从而限制了IL17信号,抑制了嗜中性粒细胞向向肺部的浸润。而GO富集分析也发现表达ACE2的II型肺泡上皮细胞在健康状况下本身以表达支持病毒扩增的信号,包括SLC1A5、CXADR、CAV2、NUP98、CTBP2、GSN和HAPA1B等[23]。这些可能暗示当-nCOV入侵表达ACE2的II型肺泡上皮细胞时,这些细胞本身也支持病毒的扩增,这就导致病毒滴度可以在爆发短期内可迅速升高。而当这些表达ACE2的II型肺上皮细胞耗竭之后,STAT3和IL17信号更加活跃,招募嗜中性粒细胞到肺部,而这些大量浸润的嗜中性粒细胞又会通过ROS和NETs途径造成组织损伤。这或许可以是感染后期浸润嗜中性粒细胞上升,出现组织损伤的一种解释。
之前抗击SARS时所设计的相关药物也被用来尝试治疗COVID-19。研究人员以VeroE6细胞系(ATCC-)评估相关药物对于SARS-CoV-2的治疗效果。结果认为雷姆昔韦和氯喹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27]。蕾姆昔韦作为一种腺苷类似物,可整合到新生的病毒RNA链中并导致过早终止;而氯喹可通过增加内环境pH值以及干扰病毒细胞受体的糖基化水平来阻断病毒感染。对于嗜中性粒细胞造成组织损伤,我们或许可以借鉴某些病原进化出的拮抗NETs的机制[28]。链球菌在感染机体后,会释放出DNase,可以水解NETs的类染色质结构,从而破坏NETs。而HIV-1感染机体后,会促进释放IL10,从而抑制NETs的形成。因此,适量的外源DNase或IL10可能有助于缓解COVID-19患者的组织损伤情况。同时,由于患者的粘膜屏障系统出现损伤,补充外源抗生素可能有助于或者抵抗外界其他病原的感染。而针对嗜中性粒细胞介导ROS导致的组织损伤,有研究人员提出可采用抗氧化剂药物来缓解对血管壁伤害,同时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29]。常见的抗氧化药物以维生素E和维生素C为主要成分,而近来包括金银花、小柴胡、银杏叶和甘草酸二胺等的中草药也凭借抗氧化功效成为抗击ROS反应的一种方向。
参考文献:
1.人民网
转载请注明:http://www.xshis.com/xyxc/60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