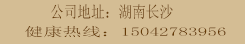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小血管炎 > 血管炎症状 > 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进行性发展的危险因
当前位置: 小血管炎 > 血管炎症状 > 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进行性发展的危险因

![]() 当前位置: 小血管炎 > 血管炎症状 > 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进行性发展的危险因
当前位置: 小血管炎 > 血管炎症状 > 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进行性发展的危险因
本文原载于《国际脑血管病杂志》年第6期
颅内动脉扩张延长症(intracranialarterialdolichoectasia,IADE)是一种异常的动脉病变,其特征是大脑动脉的异常延伸、扭曲和扩张。IADE最常见于椎基底动脉系统,近年来对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vertebrobasilardolichoectasia,VBD)的研究也更多[1]。VBD是一种以基底动脉或椎动脉颅内段异常扩张、延长、扭曲或成角为特征的呈进行性发展的脑血管病变[2,3]。既往曾被称为"椎基底动脉系统迂曲"、"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巨大延长的动脉瘤畸形"、"动脉变异及梭形动脉瘤"等术语,直到年,Caplan对VBD的概念进行了修订,并取代了以往的术语[4]。VBD进展是指基底动脉直径变化2mm,或是基底动脉侧向位移或分叉高度增加[5]。目前尚无明确治疗措施来防止动脉扩张和延长,临床上多为对症支持治疗。VBD的临床预后较差,致残率和致死率高[5,6]。因此,分析及总结VBD进行性发展的危险因素以指导VBD的临床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1 流行病学
VBD在一般人群中的确切检出率尚不清楚。根据研究人群的不同,VBD的检出率介于0.05%~18%之间[7],在首次卒中患者中的检出率约为2%,在后循环缺血性卒中患者中的检出率约为3.7%,在接受常规MRI和磁共振血管造影的无症状日本人群中的检出率约为1.3%[7]。
2 临床表现
VBD的临床症状表现为急性卒中、脑神经受压、脑积水、蛛网膜下腔出血和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3,8,9]。Shapiro等[10]对例VBD患者进行的系统评价显示,例(34%)表现为缺血性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例(28%)表现为脑干压迫,31例(7%)为脑出血或蛛网膜下腔出血,例无症状(30%)。根据现有的研究报道,VBD的临床表现可总结为以下4类:(1)无症状;(2)急性椎基底动脉区缺血;(3)与脑神经、脑干或第三脑室受压有关的慢性进展过程;(4)血管破裂所致的颅内出血。
3 自然史、转归和治疗
多项研究表明,VBD是一种进行性发展的疾病[5,11],其长期预后主要取决于诊断时病情的严重程度及其演变特征。Passero和Rossi[5]的研究表明,VBD患者在随访期间血管病变程度加剧,致残率和致死率高,最常见的原因为卒中。目前对VBD本身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可用的治疗方案通常旨在治疗VBD相关并发症[6,7]。
4 VBD进展的危险因素
4.1 椎动脉优势(vertebralarterydominance,VAD)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年龄和伴有VAD是VBD发生和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12]。优势椎动脉是指直径较粗(双侧直径相差≥0.3mm时)或与基底动脉衔接接近直线(双侧直径接近时)的一侧椎动脉[13]。VAD组VBD检出率较非VAD组增高近1倍[12],其原因可能与VAD的不对称血流使基底动脉血管壁不同部位承受的壁剪切力不同有关。血管内皮细胞存在多种血流机械感受器,例如细胞表面整合素、质膜微囊信号体、机械敏感性离子通道等。这些分子感受器可感知血流信号改变,将机械信号转化为分子信号,然后通过多种具体机制尚不明确的通路传递至平滑肌细胞,引起平滑肌细胞增殖、迁移和收缩功能改变,从而在血管重塑方面发挥关键作用[14]。血管重塑最终导致血管壁变薄,血管逐渐扩张,直径增大。依据拉普拉斯原理,管壁周向张力随着血管直径和血管内压力的改变而改变,如果血管内压力不变,则管壁周向张力与血管直径成正比,因此促进血管进一步扩张[15]。
4.2 低剪应力和炎症反应
血流动力学改变可导致血管扩张。韩金涛等[15]采用流体力学计算方法进行三维数字仿真模型进行的研究显示,VBD患者基底动脉内血流动力学发生改变,在双侧椎动脉汇合部及基底动脉尖段表现为低壁面剪应力区,并且与高壁面压力区相吻合。Brinjikji等[16]对稳定和不稳定椎基底动脉瘤及梭形动脉瘤的血流动力学特征进行的研究显示,低壁面剪应力与动脉瘤进展有关。不稳定椎基底动脉瘤存在低壁面剪应力和低流速区域,并与动脉瘤局部扩张和高壁面压力区共存。
低剪应力可通过诱发炎症反应、促进细胞凋亡等机制引起血管重塑。Zakkar等[17]的研究显示,剪应力对血管内皮炎症信号转导具有调节作用,低剪应力可导致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proteinkinase,MAPK)促炎信号转导通路的激活,调节平滑肌细胞表型和微RNA(microRNAs,miRs)的改变促进炎症反应。异常血流模式引起的低剪应力可诱导产生不同的miRs,例如miR-、miR-92a和miR-,抑制Krüppel样转录因子2和促进活化蛋白-1的转录活动,进一步促进单核细胞活化和巨噬细胞形成,上调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8、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necrosisfactor-α,TNF-α)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chemotacticprotein-1,MCP-1)等促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此外,体外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共培养系统研究显示,异常流动模式可能导致平滑肌细胞相关基因表达下调,并诱导平滑肌细胞更多地向促炎表型转变(表达IL-8和MCP-1)[17,18,19,20,21]。
低剪应力通过特异性促进TNF-α介导的MAPK信号转导而发挥促进炎症反应和细胞凋亡的作用[22]。TNF-α有2种受体:TNF-α受体(TNF-αreceptor,TNFR)-1(p55)和TNFR-2(p75)。一般情况下,TNF-α介导的信号转导主要通过TNFR-1发挥作用。低剪应力通过促进TNF受体相关因子-2(TNFreceptorassociatedfactor-2,TRAF-2)与TNFR-1结合,特异性促使MAPK(特别是p38和JNK亚族)激活而促进TNF-α介导的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ascularcelladhesionmolecule-1,VCAM-1)在内皮细胞中的表达[22,23,24]。VCAM-1又称CD,其可溶性形式为sVCAM-1,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的一种黏附分子,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膜上,受促炎性因子刺激时表达上调,可与单核细胞表面的整合素α4β1结合,介导单核细胞与内皮的黏附,促使单核细胞游出继而浸润至血管壁及其周围组织,然后参与炎症反应、免疫调节、凝血与血栓形成等多种病理生理学过程[25]。
在外向型血管重塑中,巨噬细胞浸润至血管壁并且伴随着金属基质蛋白酶(matrixmetalloproteinase,MMP)-9的表达[26]。弹性蛋白酶诱导VBD小鼠模型研究显示,其血管病理学表现为动脉壁延长扩张、内弹性层破坏、肌层介质不连续、炎症细胞浸润和MMP高表达[27]。弹性蛋白酶诱导血管内弹性层破坏可能是VBD的起始因素,随后出现巨噬细胞和炎症细胞在中层浸润并分泌MMP-9和MMP-12导致细胞外基质和弹性层降解,最终导致VBD进一步发展[28]。VBD是最常见的IADE类型,而IADE与血清MMP-3低水平和MMP-3基因启动子区5A/6A多态性等位基因的表达有关,其中以5A/5A基因型最为显著,其与MMP-3基因启动子区活性增加和动脉壁MMP-3高浓度聚集有关[29]。MMPs表达过量可能过度降解细胞外基质,从而导致血管壁强度的破坏和扩张。
以上研究表明,扰流导致的低剪应力以及诱发的炎症级联反应导致血管壁重塑,进一步导致血管弹性减弱或丧失,最终出现动脉延长扩张的表现。
4.3 高血压
临床调查研究显示,VBD常见于高血压人群。体外研究显示,机械拉伸可诱导TNFR-1在平滑肌细胞膜中的聚集和增加TRAF-2与TNFR-1的结合,并使细胞对JNK和p38介导的细胞凋亡产生敏化作用[29]。具体而言,25%面积变化的循环拉伸作用会导致JNK和p38持续激活并诱导平滑肌细胞凋亡,而7%面积变化的循环拉伸作用仅会诱导JNK和p38短暂性激活而不引起明显的细胞凋亡。使用特异性抑制剂阻断JNK和p38通路可将循环拉伸作用诱导的细胞凋亡从%降至90%[30]。正常机体血管搏动压力引起的动脉血管循环拉伸在2%~18%之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肱动脉直径较正常人显著增大,而高血压患者的视网膜动脉平均压力与直径成正相关。因此,高血压可导致主要动脉和视网膜动脉直径增大15%~35%,25%的拉伸作用可能与高血压的病理生理学有关[31,32]。血压升高引起的动脉调节可阻止平滑肌细胞迁移,从而使中膜失去增强平滑肌层所需的细胞成分。此外,血压的慢性变化可能导致部分血管内弹力层退化[2]。因此,在合并内弹力膜广泛缺陷以及中膜网状纤维缺乏的VBD患者中,高血压会导致管壁进一步扩张,从而成为促进VBD发生和发展的危险因素。
4.4 动脉粥样硬化
血流动力学改变可诱导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单向剪应力具有抗炎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而血流紊乱则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血管炎症和局部分布有关[33]。YAP(yes-associatedprotein)/TAZ(transcriptionalcoactivatorwithPDZ-bindingmotif)是一种感受机械刺激的传感器,包括拉伸、细胞密度等[34]。YAP/TAZ靶基因(CTGF和CYR61)在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高度表达[35]。层流可激活整合素,调节整合素-G蛋白亚单位Gα13-RhoA-YAP通路,促进YAP磷酸化,抑制YAP/TAZ活性,减弱JNK信号转导和相关炎性基因表达,从而减少单核细胞对内皮细胞的黏附、趋化和浸润,延缓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相比之下,动脉扰流则会诱导内皮细胞YAP/TAZ活化,增强JNK活性,促进炎症反应和动脉粥样硬化形成[36]。动脉粥样硬化早期表现为脂质浸润和内膜增生,后期则表现为弹性纤维变少、平滑肌萎缩、内膜斑块和血栓形成[4]。扰流导致的高壁面压力作用于丧失弹性的血管壁,进一步导致血管扩张、延长和弯曲[36]。
4.5 感染和免疫性疾病
病例报道显示,VBD与感染和免疫性疾病有关,感染病原体主要为梅毒螺旋体、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和HIV[37,38,39,40,41]。Lodder等[37]最早于年报道了1例梅毒感染引起VBD的病例。近年来有研究显示,HIV感染后引起的血管炎症可诱导颅内动脉血管重塑,引起中膜变薄和管腔变大,最终导致IADE[38,39]。Nagel和Gilden[40]的研究显示,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后机体发生血管炎引起血管重塑,病理学表现为内膜增厚和内弹力板层断裂,最终导致血管弹性减弱或丧失,从而表现为动脉延长扩张。Toyoshima等[41]认为,VBD可能是IgG4相关免疫性疾病的表现之一。不过,阐明感染和相关免疫性疾病在促进VBD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仍需更多的临床和病理学证据。
4.6 其他危险因素
VBD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许多危险因素相似,包括高龄、男性、高血压、吸烟和冠心病史等[6]。在Passero和Rossi[5]对例VBD患者进行的研究中,男性例,女性38例,年龄10~88岁,平均(60.5±11.6)岁,高血压例(64%),糖尿病18例(12%),高脂血症57例(37%),吸烟43例(28%),酗酒25例(16%),既往的冠心病史15例(10%)。椎基底动脉非囊形延长扩张动脉瘤和延长扩张梭形动脉瘤均由VBD演变而来,因此两者形成和破裂的原因也是VBD进展的危险因素。椎基底动脉动脉瘤的形成与男性、高血压、高脂血症和高龄有关[42];而椎基底动脉动脉瘤扩大的危险因素包括动脉瘤直径、动脉瘤形态和存在有症状占位效应[43]。
5 结语
VBD是在先天性血管结构异常或基因缺陷的基础上,通过后天各种危险因素(VAD、炎症、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危险因素、感染、免疫性疾病等)加重血管结构改变,后者造成的血流动力学紊乱又进一步诱发炎症反应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病理学改变,如此恶性循环,促使VBD不断发展,直至出现相应临床症状。
参考文献略
张春燕等赞赏
长按北京中科医院荣获品牌影响力企业荣誉称号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
转载请注明:http://www.xshis.com/xyzz/39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