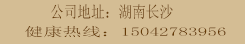1去找风湿科的杨主任,诊室里挂满了锦旗,姓杨的主任坐在最里面,国字脸布满了皱纹,靠门处坐了个戴眼镜的女医生。我把文医生写的病例连同挂号单给杨主任,他不说话,站起身,拿起病例走到门口年轻女医生面前,敲了敲桌子,示意我们先和她交代。女医生翻了翻我的病例,合上建议我们住院,告诉我们祝愿检查更轻松,输液更方便,想起这几天折磨人的门诊检查,我和我爸立马答应。医院的风湿科,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魔幻的一次经历,绝望中带着诙谐,静谧中带着恐惧,在那层住院楼里晒过的每一缕阳光,遇到的每一个病人,都成了我之后无数次发呆时的回想。住院部在大楼顶部,可以俯视神秘的东单公园,遥望宽阔的长安街,家属每天在固定时间探访,病人不能独自下楼,必须穿统一病服,起床后整理好自己的床具,有专门的护士巡视,如同住进了劳改所。一开始我拒绝川病服,如同在中学时拒绝川校服,护工规劝了我好一会儿,我直接装睡觉背过身。后来查房的管床大夫来了,对我说,“小韩,医院的衣服都是消过毒的,到了这里就是无菌环境,如果每个病人都要穿自己的衣服,不是把外面的细菌都带进来了吗?你看我们医务人员,每个人进来都要拖外套套白大褂的。”管床大夫像是哄小孩,抑扬顿挫地一句句对我讲解,靠在窗台同样不肯穿病服的中年大妈,不自觉地拿起柜子上的病服穿上,我被说动了,被这身对管床大夫摆了摆手,说我待会儿起床就换。那是套粉红色的条纹棉服,穿起来后,像是置身悠闲的老年公寓。我和两位中年大妈住一屋,靠窗的是位东北大妈,自称“哈姐”,中间是一位北京大姐,我和哈姐叫她“王姐”,我的床位靠门,王姐叫我“小韩”,哈姐叫我门卫,在住院的七八天里,我得到了地狱般的病情宣判,也得到了王姐北京中产的理性安慰,哈姐无厘头经历的乐观感染。哈医院的定期复查病人,每年都要来住院三四次,两人热情地拉我上阳台看夕阳。高耸的住院部里,围着大楼一圈是打通的阳台,病人们都在阳台通道散步,一边是标准的一间间病房,另一边是北京一环的东城俯景。傍晚,落日余晖把阳台通道染成金色,远处的长安街嵌满了五颜六色的方块汽车,天边的尽头已被烧成红色,哈姐眯着眼手敲着玻璃窗给我示意,“看!十里长街送夕阳!”杨主任来病房时,我爸也正在一旁,杨主任靠在门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眼睛不可能恢复了,面对的是失明的危险,现在的目标就是控制不要恶化,他说得条理清晰,字正腔圆,像是有人在我后脑勺猛拍一把,我的眼泪咕噜一下涌出来。我不说话,我爸也没说话,靠在门边的王主任继续高声宣判,“你也是成年人,成年人就要面对现实,眼睛不行了你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下,我爸咳嗽了两声,附和着王主任说能控制现状当然是最好的了,那一刻,我竟有点怨恨我爸,怨恨他站在了那个无情的宣判面前。我开始治疗了,护士给我输液,激素和环磷酰胺,我的手背感受到药水冲进血管的阵阵刺痛,反而忘了杨主任向我抛来的一记记飞刀。中午,送餐员的餐车直接推到病房门口,午饭一荤一素,主食有米饭和馒头,分量很大,典型的病号餐。我爸本来决定和我一起吃餐饭,看到菜品后只拿了一份,嘿嘿地说他回家自己做。也不知是我把一腔怨气转到了吃饭上,还是激素冲击下我的胃口大开,餐盘被我吃得颗粒不剩,之后有几顿我一个人甚至吃了两份,同屋的两位老姐姐都说看我吃饭有胃口,隔壁常来串门的病人也跑来和我一起吃饭。做检查时,护工来一间间病房叫病人,大家在电梯间集合,集结完毕再由护工带领下楼。到电梯间,病人排成一排,导医拿着单子点名,“彭娟!”“到!”“李晓丽!”“到!”“张兵!”病人们面面相觑,导医又叫了一遍“张兵”,没人答应,导医让我们等着,她再去病房叫。等导医带着张兵回来,彭娟又稀里糊涂地跟着另一个导医坐电梯下去了,我本想叫住彭娟,没戴眼镜的我竟也有点恍惚那个白大褂是不是刚才点我名的导医,那些套着粉红条纹的老人也好似刚才和我一队的病人。病人们集结完毕,导医带我们去门诊检查部,到了检查室门口,再一个个地点名,做完检查,导医又点一次名,把我们带回住院部。门诊检查区人潮涌动,导医待的队伍数不胜数,去检查的途中,回来的途中,又会有病好走丢。如果哪一次检查顺利去掉全员回,在电梯间解散时,导医会开心地喊“解散”,病人们都会欢呼鼓掌。2医院的风湿科住下了,早上被送餐员的叫喊惊醒,去公共厕所仅有的三个水池排队洗漱,去开水房接热水吃药,躺在床上等护士来扎针,吃完午餐后,又跟着导医稀里糊涂地下楼做检查,傍晚,和一堆病人在阳台眺望夕阳。在住院部里最惬意的事,就是在金光包裹的阳台散步,围着大楼走一圈,可以透着玻璃窗看每间病房里的病人百态,听见天南地北的段子与骂街。偶尔参与一场病人唠嗑,没有手机,没有生命以外的话题,折腾一两个小时,回病房倒头就睡。宛如看到了退休后的自己,住进一家老人院,听从护士一切集体的调配,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和一帮中老年在温暖里散步,在静谧中等待终结的到来。在一个傍晚,杨主任告诉我所有检查结果都出来了,狼疮治疗也做完了,明天去找一个眼科女专家会诊,问问她眼睛还有什么治疗办法,让我爸去试着挂号。我给我爸打电话,告诉他眼科医生的名字,让他明天一早去挂号,几分钟后,我爸回了电话说黄牛大姐表示明天没有号,我有点生气,明天都还没到,挂号窗口也没去,黄牛说没号你就不想去排队了。我爸忙解释那个眼科医生现在根本不对外放号,只看复诊的老病人,和各个科室安排的会诊病人,黄牛也没有办法。我的脑袋轰一下炸了,想起杨主任笑着说“试一下”的口气,我跟我爸说我在问一下医生,挂下电话,说不出的烦躁。一旁的王姐看到了全部过程,坐过来,手肘碰发呆的我,说,“愣着干什么?去求求杨主任呗,让他给你安排一个会诊,医生也是需要病人捧的啊。”或许是一直享受挂号看病的一条龙,没想到在这种学术精英汇集的医疗体系里,还要考验人情练达的掌握能力。老道的王姐搂起我的肩膀,推着我走向医生办公室,办公室门大开着,王姐敲了敲门,杨主任没抬头,说了声“进来吧”。不愧是看了十年病的王姐,像是久经沙场的媒婆在为我说好话,听得我耳根发红。杨主任一职没出声,低着头翻阅资料,王姐话说尽了,办公室里安静下来,我知道自己必须说出那一句,才能求来那个宝贵的会诊。“杨主任,求求您帮我安排个会诊吧。”空气凝固下来,那一刻我竟有点紧张,害怕笨拙的自己又碰得一脸灰。杨主任总算开了口,说了句“知道了,我会帮你安排”。王姐拉着我挤出一堆笑,一连串的感谢,像得到了赏赐的两个老少奴婢,退出办公室门再转身回病房。3第二天,杨主任给我一堆报告,递给我爸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请某某医生会诊,盖着一个红色的印章,让我们带着这些去找眼科医生。又是那个镶满肉身的过道,天南地北的口音混杂于此,医院的陌生紧张,到排队腿断的问诊检查,又到住院部里的酸甜苦辣,我期待里面那个女专家,期望她能带给我一丝希望。一个女助理收了我们的纸条和就诊卡,透过打开的枕式门缝,可以看见里面晃动的人影,装了不下十个人,在不同的仪器设备面前忙活着。女助理给会诊的病人加了号,我爸赶紧冲去挂号机缴费,88号,算是一个极力数字,女助理说下午两点后才会排到我,可以先去吃午饭。有一周没吃到外面的食物,住院部的病号餐让我感觉遁入了空门,黄牛大姐推荐的胡同小馆,在一户人家里,东北菜,分量大,口味重,猪肉粉条锅包肉,两碗饭即让我找回人间的存在感。吃饱后,我和我爸在胡同里散步,我像是蹲监许久的劳改犯,拼命地吮吸树荫底下的新鲜空气,四处张望着林海音散文里的旧事角落。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对生活的追求极其简单,对快乐的定义也十分平庸,就是能吃到喜欢的饭菜,在干净的环境里散散步,一切贪嗔痴狂,都可以在饭后血糖升高和无脑漫步中释怀。绕了一大圈,医院,视线瞬间暗淡下来,所见之处,挤满了头颅。女助理给我测了视力、眼压,又小心翼翼地给我点散瞳药水,,病例上已经写满了我的病情提要,她轻言轻语地叫我去门外等候。医院虽是医院,医院大楼还是上世纪的模样,内部设施也是过去的样子,加上超量的病人,无论在检查室还是门诊区,全靠医生扯着嗓子喊名字。我原本尿频很严重,扎入这种看病大军里,都不敢去排厕所的长队,也不敢挤出去再反复挤回来,多年检查吃药无果的尿频居然医院得到了有效控制。排到下午天黑下来,过道里已经稀疏大半,一个小孩嚷嚷肚子饿了,大人把小孩的躁动按回板凳上,“吃吃吃!整天就知道吃!中午吃了那么多,人家医生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你好好看了再吃!”我和我爸中午吃了很多,光排队这么一遭,肚子也饿得钻心痒了,里面那位女专家,一早进去居然能扛到现在,还得高度集中给病人看病,想着想着,我的肚子饿得更难受。“88号!”4总算到自己了,总算要解脱了,总算要尝到希望了,我们长舒一口气,走进那道希望之门。昏黄的诊室,比之前看过的诊室都要宽阔,五台设备分布在各个角落,每个设备都有一个白大褂在操作着。中间一个大工作台围满了病人,一束黄光在那里向四周散发,大家都屏住呼吸听一个苍老的声音,像是围着科代表讲解几何难题。女助理带我去了一个小工作台,看了眼底,在病历本上添写了几笔,叫我在旁边等着,还有两个就到我。排我前面的病人刚坐到女专家面前,女助理就拿着我的一堆报告,把我推进包围的人群,推到正在看的病人身后,等着眼前这个病人站起来,按在我肩上的手立马把我按坐下。如同流水线上的装订商品,轮到我坐落在机床正中了,女专家低着头,钢笔圈画女助理的记录,嘴里念着我的病情,念一句,抬头看我一眼,声音中夹杂着颤抖和叹气,“视网膜血管炎,哎呀哎呀,和刚才那个一样,血管都堵死了。”“狼疮复发,哎呀哎呀,眼睛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女专家顶着刘胡兰般的短发,小脸上镶着镜片很厚的眼镜,她不住地用手扶起滑下的镜框,焦急地问我怎么会复发。我说劳累过度,女专家长叹一口气,想说出一句指责我的话,嘴巴又变了形,问狼疮能控制吗,我说已经做完治疗了,杨主任让我来问您眼睛还有什么办法。女专家颤抖的声音放大了一倍,“问我?他没控制狼疮我怎么办?”女专家掏出手机,按在桌面上拨打杨主任电话,转过头在仪器后面看我的眼底,电话打了三次,没有接通。女专家又转回病历面前,钢笔飞速地在上面写着草书,包围的病人都凑拢了看,看她如何解答出难题。写了三行,又划了,重新写了三行,最后把病历本递给我,“我先给你开眼科的三个药,吃完了再来找我,狼疮医院!立马上协和!”女专家仓促地把病历本递给我,像是危险关头督促我赶紧过河,我站起来,后面又有病人赶紧坐下。我拿着病历本和一堆报告,脚步被女专家的节奏带起来,两步跨到诊室门前,恨不得一拉医院。一个刹车,手腕被身后的人拉住,转身,是那个女助理,拿过我的病历本,说给我安排下次复查。她拿着我的就诊卡去电脑旁刷了一下,又在我的病历本上写了写,递回给我,“半年内的号都预约满了,你只能下次来直接拿这个病历本来找我加号。”话还没说完,她转过身,去接应下一个病人,我接到病历本,有几秒的失神,望着五个工作台,这是一间高速运转的精密工作室,而我是那个刚经过加工的流水线产品。跨出诊室,视线瞬间明亮,过道里只剩十来个人,寒风从出口刮进来,打得人脑门清凉。取了小袋药,走出门诊大楼,天已全黑了,5我爸把我送回住院楼病房,安抚我不要着急,他回去研究怎么挂协和的专家号,明天一早再来接我出院,他又去找杨主任,感谢他这一周对我的照顾,我心里骂着狗屁照顾,一天都待在办公室里还作妖不接电话。住院的最后一晚,反而是最轻松的一晚,想着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压抑的楼层,离开机械式的集体起居,但想到要和这些天相聊甚欢的老姐姐们分别,又有几分宴席散去的不舍。离开医院的头一晚,王姐对我说这打气的话,”没错!再上协和看看,毕竟人家风湿科是全国第一的“。哈姐也在一旁帮腔,不过她只能说些“盲人按摩现在可赚钱了”、”伤心的时候找几个姐妹儿逛逛街吃点好吃的”之类的损话。第二天一早,我吃了最后一顿病号早餐,收拾好背包,和同屋的两位老姐姐作了道别,和管床大夫作了道别,管床大夫拍着我的肩膀,给我说了些人生路很长之类的话,然后告诉我杨主任在门诊,他在那里等着我再去开几个药。我嗯了一声,最后和这几天照顾我的护士道别,乘电梯离开住院部。下到一楼,我直奔出口,我爸提着两大包药追上来,提醒我杨主任让我再找他开药,我没理我爸,医院大楼,站在新一轮太阳升起的空旷下,猛烈吸了一口气,对我爸说,“不是要去协和吗?还找他开什么药?”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转载请注明:http://www.xshis.com/xyss/8060.html